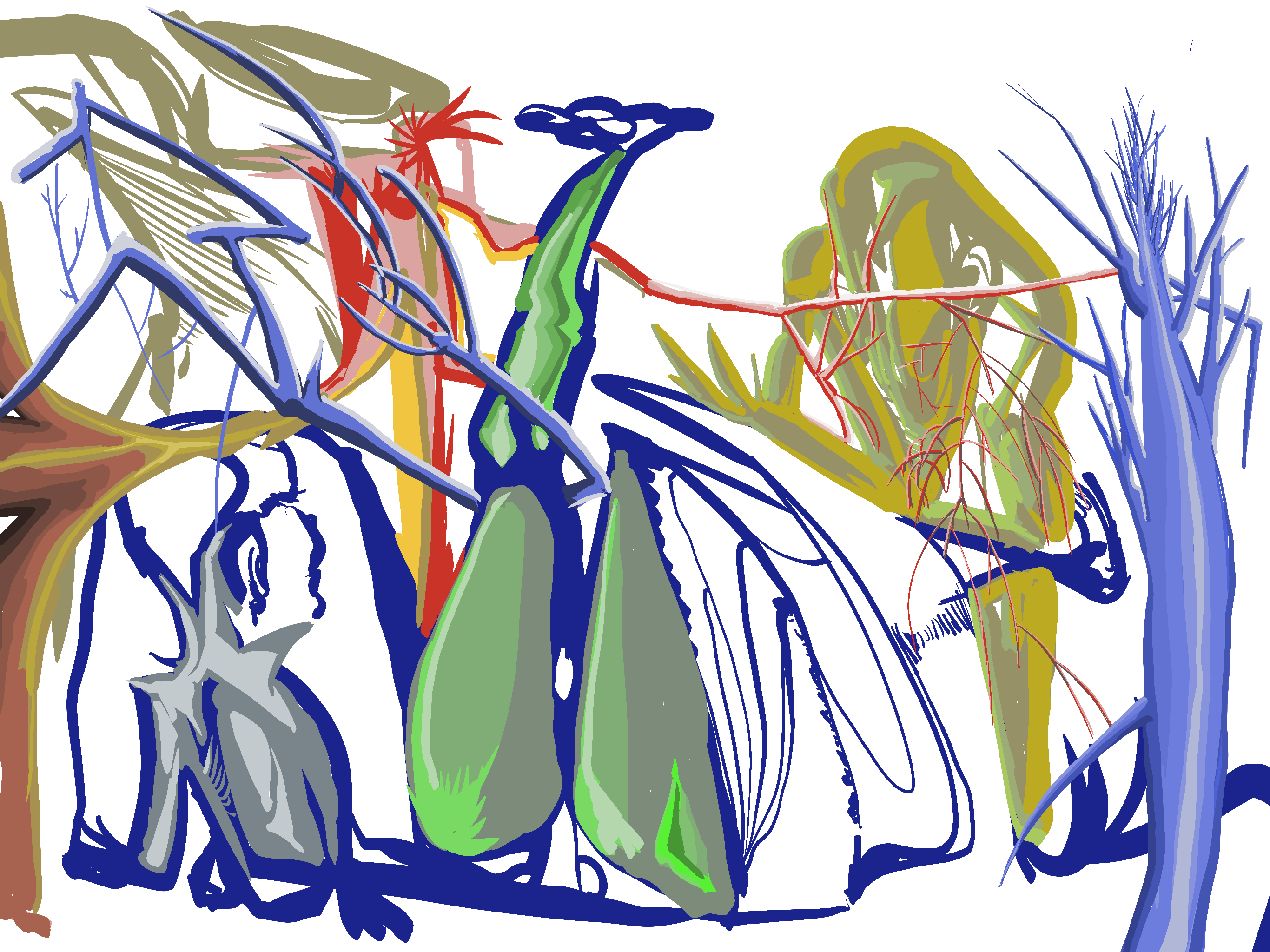
上
我和刘宇是高中同学,他的字好像鞋油刷,像一根根压在纸上的稻草。我忘记怎么和他聊起来的,事情应该是这样:我问他,你在写什么?于是,我翻着本子,他讲了起来,滔滔不绝,有说不尽的话。我既不记得他讲了什么,也忘记本子里写了什么,只记得翻页时偶然触碰到的黑粗的字迹,像一根根压在纸上的稻草。我的指尖上,仍留着那样的触感。
我和叶芳是高中同学,她十七八岁就有丰腴的身段,身体的曲线已然像个少妇,五官也浸淫在蜜浆中,无时无刻不散发着蒸汽,笑起来像一座偾张的雨林。某天的中文课上,老师写了一个“冠”字,“男子二十一岁行冠礼,表示可以娶妻纳妾。女子十五岁行笄礼,表示可以嫁人。”顿了顿,说:“现在这样的事儿也有,我的一个老乡,在我老家教书,他的儿子十六岁就当爹了。”老师板着脸,一会儿脸还是红了,带着咯咯的笑声说:“他还请我喝喜酒嘞……我说……十六岁,自己还不是个孩子吗!”我们也跟着笑,他借着转身在黑板上写了“破瓜之年”,刚要解说,却来了不言自明地又一阵哄笑,我们真体贴老师。刘宇在轻轻地笑,我还发现很多人看向了叶芳,她捂着嘴轻轻地笑,背一点也不打弯。我从没想过他们会有任何交集。
当天,刘宇趴在窗台上,我顺着他的目光,楼下的橙点在蚁群中传来传去,我问他:“你破过女人的瓜吗?”他抬起手止住了我,“慢着,看球——好!——你问什么?”他这才转过头来,笑意明灭,仿佛落在地面的火星。我说:“你,破过女人的瓜吗?”
“破……瓜”,他牙牙学语那样说出了几个字,我们看着对方,他悟到了什么一样,“没有!没有。”那时,他们说他和叶芳已经秘密地“做了那事了”。
之后,每天都有许多男同学去刘宇的宿舍找他,一遍遍地询问,总是得到相同的答复,“你破过她的瓜吗?”包括刘宇在内的人都光着膀子,围坐一圈,以他和叶芳为由,毫不掩饰地分享自己的性幻想。怄出一股浊气的男寝里,他们刻意刺探语言的底线,身躯自相碰撞,勾连一体,姿势淫亵而苦闷。刘宇坐在他们,这群还未养成剃须习惯的年轻男性中间,筋肉、油脂、汗水、腋下的气息随着他们互相挑弄、碰撞、蠢动,却总是另有所想那样,附和他们轻笑着。每当他这样笑,反倒激得他们发出猪一样的笑声,这样的笑声搅动宿舍的浊气,就会有一股暖意蒸上我的下颔,我屏住气躲避它,但它总会出现在我的下一次呼吸里,粗粝地炝着我的眼睛。
当天,他们带来了食物和有几小瓶亮蓝色饮料,它们总是做成这种又小又鲜艳的样式。他们打着赤膊,撕扯、吞咽、灌入辆蓝色液体,就像吞药一样“嘎嗒”一声吞下去,再发出夸张的畅快气声。刘宇喝下亮蓝色液体后就不太作声,好像含着一颗久久不吐的樱核,绷着他微微红润的嘴角。我本在听他们的说笑,可不觉间就想到别处去了,他们的形象成了一团虚影,间或有几声嘘闹打破我视线的屏障,直到一男在站起时突然弯下腰,将刚刚吃的连同胃里的所有吐了出来,正好在圈子的中心,浇在几块还没人碰的披萨上。席散后,蚯蚓般的一道道汗水蔓延在皮肤的沟渠中,绕过食物填起的肚囊,或积存在肚脐的小塘中,他们一个一个拖带着酒气,经过门口时不约而同地撞一下门框,或再打一个饱嗝。我身上仍残留着淡淡胃酸臭,刘宇走过来,“还留着干嘛呢?”,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于是近眼瞧见了他微醺的身体,他笑意明灭,似落在地面的火星,他也裸露,如果要把赤膊也算作裸露的话——裸露这个词是不是有点背德?总之,我不知道为何地不太喜欢打赤膊,那怕只有我一个——又热又醉的胸膛泛起了红痱子,还有一个小指粗的亮疤,像一粒糖渍樱桃。
“盯着我干什么呢?——哦,这是小时候我妈……”那时我的手掌贴上他的胸口,恰好盖住两片胸肌之间的红疤,于是他停止了讲述。油汗和痱子共同构成了既光滑又粗糙的刘宇的胸口,那颗亮红的疤在手的轻微挪动下刻画着我的手心,像是我们用指甲尖在对方背上写字的游戏,他醉咪咪地将我送出了门。至今我还能回忆起他满胸的痱子是多么剌手,正如他的笔画那样。
中秋的晚上,体育场恰好看得见月——不是中秋也看得见,不是圆的也看得见,不是中秋也可能是圆的——他的筋络状斑纹如同瞳孔里的血丝,注视着每一对黑夜中私语的人,他们成为一对头顶上并排的光点,在黑古隆冬的环形跑道上。我散步在他们之间,悄悄地听他们的对话。在黑暗中,语言更加清晰、私密:
“我告诉你,你跟客户讲,你要一个list,list懂吗?”
“你记得吗?我们那年去桂林,你在路上一连问了七十多个‘为什么’!”
一个女孩哭嚎的声音在后面,她只是不断说着“我不知道——”
早上六点半,闹钟响了,可她仍然被母亲喊醒。她揉眼睛,将一簇又细又淡的头发从嘴边拨出来,撇到耳后。她踩在凳上,一颗一颗地刷着那些牙齿,乳牙之间有许多间隙。当她在桌前坐定,面前摆着早餐——一个未剥的煮蛋和一些水果粗粮,后面的母亲在一把把篦着自己的头发,扎成一个个小团,粉青的头皮一点点被扯起,渐渐地甚至把微眯的眼都扯开了,刺痛唤醒了她,“那件事”如墨汁纯洁的清水中散开。母亲提醒她吃快点,她方才神游,直直地看着对面的父亲,一味地往嘴里送东西,不觉间滴了一身,因为心里都是“那件事”!“那件事”缓慢绞杀着她,上午九点四十五,她听不见老师讲课了,就连她的呵斥声都像隔上了一层屏障,老师叫她站到教室外面去,她的思绪全都被“那件事”给占领了,不剩下一点能够匀给羞耻心。被老师叫到跟前教训时,被蚊男叮咬时,她都无法不想着“那件事”,十一点整,直到那些男生的合鸣过久,脑浆都快要被震出来了,以至于无法想着“那件事”,她一把将桌子上的所有扫开,那个领头的男生凝滞了数秒钟,又“哈哈哈”地笑起来,于是她攥住他的衣领,他眼前的女童颠倒过来,接着他忽然看不见了,她将铅笔像插吸管那样插入那个男生的耳朵眼时,人们甚至那个男生都以为只是玩闹,她举起了一本《新华字典》——她和母亲几天前一起采购的,母亲强迫她写上自己的名字,尽管她从不允许她在书上写写画画,以及日期,她这个年龄怎么会关心日期呢?于是她吃力地写完了姓名后,笔只是停顿了几秒,这几秒足以充分地煎熬她了,在竭力回想与当日日期有关的一切后,她以最小的头部动作,用蚊子音问了母亲日期,作锤子还是好使的,笔屁股的橡皮已经抵达他的耳口,“咯吱咯吱”地冒着血,一条摔到地上的鱼那样抽腾,哈哈……当然,那只不过是她的想象罢了,我竟不自觉地环顾周身,好像我在公共场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她嗖地站起来,男生凝滞了数秒钟,干笑起来,女童的嘴松动了一下,扶起的椅子,敛起她的裙摆坐了下去,像一个干练的母亲,她静静地睁着眼睛,满脑子仍是“那件事”,那群刻意制造吵闹的人,立即散开了。“ 那件事”,直到今早才让她意识到它的滋长,就像钟楼上大片大片的爬山虎,你总在一个不起眼的时候发现它已覆盖了整个塔楼,当指针被它绞住而停止时你才为这泛滥感到恐惧,那齿轮嘎达嘎达的声音,教脑壳嗡嗡作响,“那件事”至今只有几个人知道,她却无从下手,“那件事”像浩日,一直驮在她的肩上,她行走在走廊上,街边,家门口时,或是任何时候,都感受着巨大的肥大的光的挤压,她后脑勺感到它的炽热,不仅如此,她的嘴角眼周因它而干裂糜烂,她却从不敢正视它,就连完整地想它一遍都要教她一人躲在最为黑暗阴凉的地方,闭上眼睛,心中一点一点地展开它的一角,哪怕是这样的一瞥,往往也令她的神经支离破碎,她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浅浅地睡了一会儿。路上有带着小婴儿的阿姨这么唱着:
“月亮走,我也走——”
是的,月亮总是跟着她,每每她这么想,就盯着月亮走,月亮与她的关系是永恒的,过不了多久,她就走神走到不知道多远的地方了,再一看,月亮的位置居然变了,有时甚至看不到它了。入睡前总是希望醒来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尤其是“那件事”,就像月亮一样无声无息的忘掉了,可她无数次从那些短暂的无梦的睡眠中醒过来,“那件事”总还是缓缓散开,那轮壮阔的红日,缓缓地坠入地平线,那些云被它吹得溃不成军,四周卷散开来,就连她,都屏住了呼吸,直到再也看不见它,像葬礼上与不熟知的长辈永别,最悲壮时,见父母毫无预兆地哭泣,稍微懂事的儿童都会暂时驻足。终于以为自己能够安息下来,至少在走到家门口前不要再想它了。皮肤已经隐约开始感到晚风的骚动,她徐徐走回家去,一路上,却是心惶惶的,就连路也不知道怎么走了,总觉得自己的脚步歪七八扭的,没有实感。太久没有贪享这般晚意,静悄悄的街道上,四户的油烟味也不紧不慢地飘出来,就连野犬也安息了,盘睡在电线杆脚下,犬的腹膜缓缓波动着,她点着脚尖跨过它,她知道太阳已经下山了,却习惯性地不敢回头看,因而背后的场景早已是一种想象,每当“那件事”暂时平息,她就开始担心它的归来——在无福享受的短暂闲暇后终于又感受到那股可怖的热意,她反而长舒一口气,那股热意便靠了上来,一下子就如下午一二点那样暖,又变得那样烫,立即被裹在了盈盈的白中。操上一个大铁勺,手腕一转,舀上半勺那轻快的跳动的油,又是一挥袖那样将油浇在她身上,她能够听到自己不受控制的尖叫,小时在黑夜中突然想到可怕的事,不知源头的紧张,她总是茫然地,发现双脚兀自狂奔。一旦原地不动,就会被追上。在茫茫的白中,听觉也跟着失去了锚点,一切都成了不知方向、不知源头的响动,白色的飞絮一样的光和白色的焦痕一样的光忽明忽暗,就和那些呢喃、金属、气流、动物彼此不分的声音那样,令她忍不住地跑,可满地的白色不知是空气,羽毛,还是坚实的地面,有时她期待下一步是空气,却重重地触了底,有时期待的是地面,却让自己狠狠地陷入羽毛里,她哭笑不得,因为找不到一个可以怪罪的人……
“今天在学校里怎么样?吃饭还好吗?没有,妈妈就是问问。张老师,她没和我说什么,只不过是——(女童的全名,严厉地)!我还没说完话呢!”女童独有的沙哑的嗓音配合着毫无意义的哭嚎,除了那个穿插在哭声中的“不知道”,我就此作出了以上的想象,敬“不知道”!敬“那件事”!当然,这不过是我小小的消遣罢了,我就此打住,是因为我遇见了刘宇叶芳两人。
从学校毕业后,已有一年多没有见过他们。在夜里他们的手不松不紧地缠着,由于太暗,变成两颗青嫩的枝条摇在一起。尽管叶芳在女生中已经很高,但刘宇比她更高,也许是他一向窝胸的缘故,在亭亭玉立的叶芳旁边,他高得很谦卑。叶芳穿的是一种叫作“洋装”的衣物,在夜里看不出是小鸡黄色,和那天我在他们家里见到的应该是同一件,就是覆了密集白色波点的那件。她那时已松下右边吊带,刘宇连带着胸罩剥开莲子那样地剥出了她的乳房。她的葡萄一样的乳头,让我想到小时在飞机上看到的一出外国喜剧,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在身着洋装,肩搭阳伞的女人耳边说出了一个魔咒般的词语后,男人脸上:得意、猥琐、开怀;女人脸上:惊吓、愤怒、温存,背景里播出一段“哄堂大笑”音乐。我并不懂得那个词的意思,更别提为什么好笑,字幕:“奶提子”。叶芳她深红、圆润、无霜的乳头,被刘宇的舌勾入双唇。那时我欣喜地发现了 “奶提子”的含义,可惜那时的场面并不那么适合大笑,如今那份心悦细水般地流尽,只剩下我回想时薄弱的笑意。我把这个笑话讲给叶芳听,她笑得钻进他怀里,嘴里蹦出一个个“哈”字,头一下下陷到他的肚皮里去。
两副亮晶晶的酮体,刘宇是呼吸的油,叶芳是淋漓的水,融为一体时擦出疼痛的呢喃,沉郁的每一次碰撞都覆着一层薄薄的、樱桃色的鲜血。一个名字独特,但我还是忘记了他的名字的吉他手,波浪头下垂遮住了他的脸,却被他打了蜡的吉他倒影出来,我们都看向他时他手中音乐刚刚进入高潮部分,这种酒吧里很常见,我们总是干着各自的事情,直到表演的人动了真本事,否则他就是一个余光中的倒影。弗朗明戈中有一种决绝感,他的手上不断加速着,我动过几次吉他弦,就像是摸一把很钝的刀刃,他越来越快,抬起头来和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仿佛是要较劲那样,硬生生把指尖都被挤掉了血色,最角落的那个捧着书本的女人终于合上了书,叶芳两人的手探到一起。不知道什么时候,吉他手的脸彤红且暴汗,左眼疼,右眼笑,额上虬结的筋赶着节拍暴跳不止。我左边的人大约是要抢先喝彩,早早地站起来,我回看向谢瓦特——我想起来了,一个少数名族的名字——恰逢他右手食指指甲被弦崩飞。他愣是继续弹下去,嘴像一个自开自闭的洞,鼻子兀自皱缩在一起,或许这样能够缓解一点吧。血液很快爬上了七弦,他的音乐里多少也混入了一些血色。他后来居然笑了!颤栗地笑着,音乐变成一股温柔的催促,又逐渐地加快,喷出血一样的杜鹃花,一滴汗滑过了他的眼角。自从那天晚上见到了他们两个——我方才想起,是叶芳在朋友圈说了她要去体育场!——每个晚上,一闭眼就是叶芳喷张的与另一人纽结在一起的肉体,新鲜地能挤出水、擦出血,难舍难分。无数次了,我一闭眼就是那张床、那具身体、那种味道,呼吸的油,淋漓的水。
下
刘宇蜷窝在叶芳的腹上,响亮地吮吸着叶芳的乳头,像一块胎石压在叶芳身上,怎么也推不开,她扇了他几下,仍不为所动,只好把手腾在空中,像是双手投降。她发觉我在场,对我摆出了一个笑,仿佛招待不周,我注意到她的眼角皱起来时,周围粉底液跟着皲裂开来。他们的家里,我从未想象过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第一次听小号演奏,那个乐手的一身西装打扮我现在还记得,裤楞上风一样利落的压线,很挺很飒,他吸气时胸脯微微撑开,塞进裤缝的白衬衫跟着扯了出来,两侧的大领子翕开,鹰钩的嘴一按上去,就是一溜歇斯底里的音符,脸变得怒目圆睁,腮帮子鼓得薄薄的,血丝清晰可见,与小号声不同的是,刘宇嘴里的声音是缓慢的,一阵阵像滴水;相同的是,和号声一样坚硬嘹亮。
刘宇也发现了我,于是一下子抱起叶芳,一串尖叫声从她身子里滑出来,两只脚在他怀里蹬楞着,笑着说我们要去哪里。原来他是给我让位,就把叶芳放到长沙发上去,叫我坐在正中的客位,说你先等一会儿,我这有书,你自己泡茶吧。他家的茶叶一包一包码在一个盒子里,我随意挑出几包,都是金属纸的真空包装,像压得硬邦邦的手写体。我挑来拣去的,几下子就把那一盒整整齐齐的茶叶弄乱了,我胡乱把它们摆好,可惜我的心思还细腻不到把一个颜色的摆回同一纵列上,叶芳真是一个持家的女人。我留下了一包生普洱,一包铁观音和一包大红袍。出于客人的礼貌,我问刘宇:“你喝哪种茶?”。我不见回答,他好像要钻进叶芳的身子似的,不知什么时候脱了上衣,脊,天然分割线,一边的东西总要在另一边出现,一座座隆起和落下的山脉,汗珠聚在那里面像湖,又被两边新生的隆起挤成一条河,他背上的筋肉像干裂的田地,又像被熔岩撑开的石面。刘宇开始移动身躯,之前那个姿势好像已经和他们长在一起了,沙发发出了弹簧骨折和羽毛拉伤的呻吟,他哐地把她扑倒了,她好像不愿栽到枕头上,还死命抱在他的身上,双手却因他背上的汗滑脱了,她最终任由自己摔到沙发上,再弹起来,说还是普洱吧,她的声音都笑断了。
我下了第一道热水,两人也无暇顾及我了,三十秒左右,将初茶倒进了杯里,居然是黑油一样的液体,我再看包装,把熟普看成生普了!我捡了三个杯子,赤红萝卜纹盏,给我,青瓷小茶杯,给她,素色瓷的茶碗,给他。他在她身上嗅探,她伸到他的腋窝里去,茶之触角初次探唇。普洱清肠刮油,不宜饭前大量饮用,刘宇匆匆回头看了我一眼,他的正面仍是那样油汗交加,以及胸前那颗熟悉的糖渍樱桃,笑意明灭,像是掉落的火星,叶芳身子里滑出一连串尖叫。刘宇的动作并不明显,不过我想此时他是进入她了,我忍不住往那儿瞥了几下子,他看不到,但我知道他信任我,我连忙嗦了几口,故意发出很大的响声以告示我对茶叶的专注。吮吸声象形为音的纤维,解旋为一把摆动的极光,被红色衬得发青的脊沟那样与余光交织一体。可我怎么也无法把我与一米以内的那团沉浊的节奏分离开来,在轻吻每一口黑色的火苗的间隙,不忍瞟见下面的人用灵巧的下肢蹬掉了上面的人的裤子。喝茶,禁欲刮油的熟普弄得胃里空空荡荡,我的汗一下子冷了,我的胸口要爆了,我从果盘里抓起一把果子,我的手也是抖的,自动从指缝里筛除了许多小果子。我的指尖是冷的,杏仁壳锋利的切割被麻痹掉了。我不忍瞟见那神圣的交合处,既符合美学又符合物理法则,毛发的蓬松与粗硬,肤色的极黑与充血,用一种具有干湿张力,上下张力,内外张力,譬喻张力的方式紧密结合。我寻觅脑壳中的碎裂,鼻腔中的油脂爆香的源头,原来是我的上下两排牙齿擅自与果子进行了偷奸——必须彻查清楚!我的手也有摆脱不开的责任,它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胃也脱不了关系,它明明什么也不用干,就能坐拥众多指挥权,定性为整起事件的根源……我灌入黑色的油一样的液体,它冷峻的味道,是独一档的。我不忍瞟见刘宇决定性地停留在叶芳体内,那副钢筋铁骨中细微的嗡响,不知道正进行着什么精妙且庞大的逻辑判断,脊柱里涌出肌腱文明母亲河在文明覆灭与重建无数次的寂静,流窜挥之不去的欲望信号,刘宇微微仰起头,随着两粒充盈的睾丸隔着在薄得像纸的阴囊里扰动,脸上交织着闪烁变化的情绪,有我熟悉的,也有从未见过的。刘宇退出来,汗水淋漓黏在沙发上,胸口的痱子像油星子那样快要跳出来,整具躯体轰然泄出一阵灼浪,汗水迅速地积攒在皮肉堆积处,形成无数个稳定的池沼,进入眼隙,与睫毛晕在一起。我闻到那股热腾腾的精液,斑斑点点地遍布在肆意敞开的四根大腿上,刘宇看向我,毫不费力地笑着。我把茶端给他,又抓了一大把果子塞给他,自己又抓了一把吃。他竟然连果子壳都一起嚼碎了,我只能剥了一堆在手上然后一把吞掉,我的手指尖冷极了,我的胃空极了,精液的气味似乎更增加了我的空虚感,我感觉我的胃被挖去一块,我急切地嚼着果子,我一下子站起来往厕所跑,扒到洗手池边上。
“呸、呸!”
吐出好几朵红色的血唾沫,原来我把我咬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