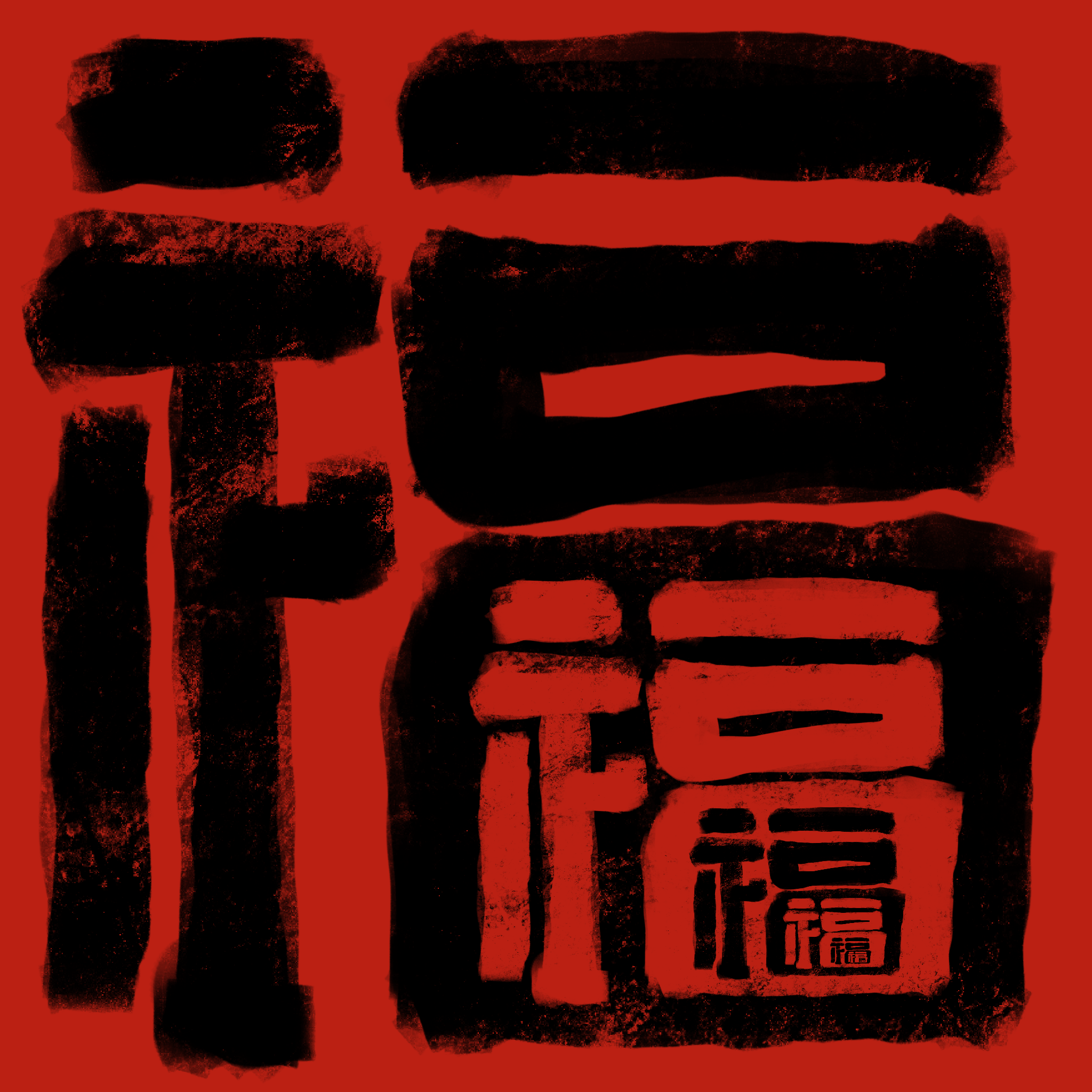
坐下来就是一整天,下身与坐垫之间已汗得不行,他总想,他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清洗这张坐垫,可每次与坐垫分离不到一刻钟,研究所的冷气就让下身回到干爽的状态,坐垫静悄悄地摆在那,让龙井觉得永远无法接近。那天傍晚,窗外已亮起日落路灯,办公室里公事公办的光加重人的饥饿感和回家的欲望,龙井发觉自己对一行代码多次失神,抬眼,三面胡乱堆砌的文件、纸张、摆件,显得自己像一个被逼到三面绝境的将军。一抡桌子,他狠狠地转向自己的背面,把一切甩在自己的正面。面前的毛玻璃里人影流动,全是下班的同事,一抖一抖,再不回到这里那样高兴。毛玻璃上的红纸上的“福”提醒他,今天是春节——严格来说,今天是春节假期第一天,他不知道春节是几号,也不想知道,任何节日都是假期,假期是可以不用工作的日子,假期是间歇性的。“福”字是一副新年印刷品,“福”的周围有一圈塑料珠子,红纸面撒了厚厚的闪粉,“福”的不同之处是它右下角的“田”,“田“的不同之处是它中间的“十”,“十”被换成了 “福”,这个“福”也包含了一个同样的的“福”,龙井数不清究竟有多少个“福”字,这种福中有福的结构似乎让他想到了什么,他狠狠地把自己转回工作台。这个“福”终究没有帮上龙井,他算了一会,最终回到同一个死胡同,此时只剩下他一个人,保安和环卫工们出没,令龙井的存在不合时宜,像是半夜忽然开灯,才发现家里遍地都是白天不见的蟑螂——家里,龙井已经到了家的门口,他不知道家里来了谁,更担心自己的妈妈,她催自己回家倒没什么,而龙井从今早就没收到妈妈的消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吃完饭了吧。龙住门把手,像握住一位挚友的手,也像是被一位挚友握住手,自己的爸爸正坐在门口的茶几的主人位上为一圈失去母亲的、失去妹妹的、失去姐姐的、失去姑姑的、失去姨婆的亲戚沏上一杯饭后的龙井,他们是混不下去的、失意的、矇昧的、讨不到老婆的表弟、年逾花甲却仍需当保安或做保姆补贴儿女家用的农民叔姨。妈妈和另外几位女性在做完了一桌年夜饭后洗着吃年夜饭剩下的碗,龙井未推开那扇凛立的黑门就看到了家里应有的样子,小孩在他脚底下旋风乱窜,如果是穿着裙子,或许会像玛丽莲梦露那样被掀起。电视机里泣血笛声,仿佛一串一串的糟心事,到了新年愈加昂扬。这种喧闹唯一的好处,是让妈妈暂时也忘记自己。门问:“你准备好了吗?欢迎回家。”龙井在门把手上的汗已经冰凉了,仿佛身外之物,回家。
妈妈撑着头独坐在餐桌前,似乎要睡着了,因为没有人,只留了头顶上一盏灯。进门后,最先看到的是花瓶里一串白蝴蝶兰,坐在妈妈临侧,一碗饭已经摆在那里了。七八个菜已经丧失锅气,结成一块,难以下箸。那碗鸭子上浮现出一层油皮,并且开始发皱,他从油皮下捞出一块鸭肉,汁水脓似地从筷子眼里跟着溢出来。妈妈做的鸭肉,一如既往地腥、柴、扎嘴,也只有过年的时候做这么一次。两人还没有说什么,妈妈看着龙井吃,龙井盯着那串蝴蝶兰,像一串挂在瓶口的脊椎骨。第一节开得最盛,也老得最早,看上去已经缺氧很久,几乎要变成透明的了,最底下的那一朵,小小的像一节尾椎,翘着一簇尖黄的芯子,边缘焦黄蜷缩,像是火中的纸片。花瓣脱落前的微微颤动,让龙井想起蝴蝶充满粘液的第一次振翅,乳牙脱离前的松动,伤口结痂时的瘙痒……那断口的新鲜,敏感得像刚脱离产道的婴儿,仅仅为他拭去胎血,也不知会带来怎样的激痛,妈妈的哭声就像是断口里湿答答的粘液,不知何时花瓣脱落,这种脱离应该是什么声音?龙井想象不到。汩汩地,轻微而不可遏制地流着。她的脸成为了哭的终点,肿成一条缝的眼睛,拱桥形黑洞的嘴,毛孔随着她的抽恸红白转换。
“拿!刀来!“他听到那天从他喉咙喷出来里像是动物咆哮的陌生的话,哭的,笑的,跑来跑去的,同样愤怒的,佯装无事磕着瓜子的全都停住看向他,
“你剁了我吧砍了我吧杀了我吧!我——”
他发不出一点声音,小孩逃窜的尖叫像是蚊子叫,他发现自己好像在找什么一样在家来回走动,泪水像粘住了眼睛。妈妈从房间出来,赤脚踏在地板上的噔噔声让让龙井脑袋发肿,她问“你怎么了”,龙井要往前走,“让一下”这声音却和刚才一样像是地狱的火焰,妈妈尖叫一声躲回房间,爸爸的叫骂声像一根根棍子抽在下巴上,妈妈总说这声音像是要吃了她一样,
“吃了我吧!你,吃了我!吃了我吧你!我——”
龙井的脚发了狂似的动起来,他扭头冲向那个比他矮很多的男人,他也在满眼通红的骂着,口水喷出来连带着几颗牙齿,牵出带血丝的涎液。龙井的手扣在胸口,他的指甲很容易就插进肉里,他一下子把自己撕成了两瓣,爸爸脸上糊满了儿子的血,眼睛都睁不开了,墙上的小裂纹长长汇合,妈妈冲出门把脸贴在墙上,大叫:“我的房子,房子!房子——”她抚摸着被爸爸的皮鞋踢疵的墙角,又嘶叫一声仿佛从梦中惊醒,跌跌撞撞冲进厨房,像一滩烂泥一样撞到冰箱上才停下,拿出抹布挤掉半瓶洗洁精在上面用指尖一点点用力擦拭地上流动的血,一阵冷风吹入,她又赶忙关掉家里的窗户,她立马汗流浃背,疙疙瘩瘩地说着“热——热——热啊”,脚与地面碰撞出噔噔噔的声音换作平常她一定全力制止。她大腿撇向一侧,屁股肉和骨头砸到地上听得人呲牙咧嘴,她的嘴张得像一个拱桥形黑洞,沙哑地哭着:“房子——房子!”,最后一声居然像小女孩的嗓子那样甜蜜。龙井的家接着爆开了,妈妈怎么喊也阻止不了。从此以后,爸爸就消失了,龙井这才突然想起,今天本来就只有两个人。妈妈的嘴越张越大,红肿的毛孔像是一粒粒芝麻,她的眼睛发成球状,眼缝密合。当所有的声音尽了,仍留下一个不停舒张的胸脯和那张拱桥形的嘴,像一具哭干的壳子,龙井怀疑她的嘴巴闭不回去了,因为这个动作维持了太久。他始数妈妈嘴角的皱纹,可发现怎么都数不清,每一次数都不一样,明明看起来就这么几根,原来妈妈也没有,自己也没有。原来没有妈妈,也没有龙井,也没有家。